人类在漫长的文明进程中发展了惊人的智慧,产生了海量的知识和复杂的文化,这些文化成果大多是通过极为艰难的探索和长期的实践才逐步形成的,所以非常宝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人类社会对知识和文化的积累、发展和传承的需要越来越迫切,相应的制度安排和保障就开始出现。在欧洲,古希腊有贵族子弟学校,教授体操、音乐和文法等。在中国,孔子以诗书礼乐授业,门下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说明制度化的传授知识和思想文化,是很早就有的事物。
人是生物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人的生物特性通过遗传传承,社会性——也就是文化,则是通过教化来完成的。生物的线性遗传特性和文化的非线性传承和传播特性,就让文化的习得变得非常重要。一般而言,人们无法轻易改变自己的生物特性,但可以通过学习和掌握文化知识来改变文化特性和面貌。一句话,对于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而言,学习文化知识的重要性是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的。
在社会划分出阶级之前,人们的知识和文化是整一的和全民共享的。随着阶级的出现,文化也逐渐出现了分层现象。列宁曾指出,在阶级社会里,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文化,统治阶级的文化和被统治阶级的文化。钟敬文在解释民俗文化时说,在传统社会中有两种文化,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在不同的使用语境中,有时也用精英文化和草根文化等说法。
唯物史观认为,人民大众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主要力量,他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发展出来的文化和知识,是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理应受到重视、保护和传承,但实际情况往往并不是这样。在世界各地我们都能观察到这样的现象:上层阶级所代表的上层文化,受到格外重视;下层阶级所代表的大众文化,则往往遭到蔑视和轻慢。这种偏向,也体现在教育体系中。与精英文化相关的知识谱系,得到系统的梳理、传授和积累,而与草根相关的知识,则被忽略甚至弃之如敝屐。在世界上许多地区,文字被发明和使用之后,往往与王权、贵族等上层文化相关联,而语言则一如既往为全体人民服务。但就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的两歧遂分而言,文与言的利用则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加剧彼此区隔的角色。
知识界关注底层文化的意识,就学术层面而言,大约是从格林兄弟开始的。在西欧,18世纪中叶出现了“民俗学”这个概念,以及相应的学科鼓吹。中国民俗学的开端,则要到五四运动时期了。北京大学《歌谣》周刊的创办和相应研究的展开,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
经过长久酝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出台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则是向国际社会正式吹响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的号角。这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度曾叫作“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o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of humanity),主要指的就是民众所创造、享有和传承的文化。这是因为国际学术界越来越意识到在人类的文明传承中,口头和书写是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语言学家李宇明说,人类80%以上的信息由语言来记录、传递、储存(《语言与人类文明》)。这等于说,人类有史以来所创造和传承的文化和知识,超过八成是记录、传递和存储在口头传统中的。所以,用“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指代民众中传承的文化,也自有其合理性。再从常理上看,在以往的教育体系中,将超过八成的文化、知识中的大部分排除在了制度化教育之外。因而,可以说,人类在总体上对自己所创造、传承的知识、文化的认识是片面与狭隘的。
在人文学术界,多少个世纪以来,精英的、上层的文化占据了舞台的中心。虽然在过去的两百多年中,国际上关注民众文化的呼声不绝于耳,但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既有格局。现在,凭借着国际性“非遗”的强劲东风,“眼光向下”的趋势开始走强。但正如俗话所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传统的惯性和惯制还在持续发挥作用,广大民众的知识和文化登堂入室的过程仍有重重阻碍。纠偏需要用格外大的力气,需要有人扮演“开顶风船”的角色。于是,我们欣喜地看到,由王文章先生任主编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辞典》隆重面世。这部大辞典,可以看作是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在推进保护非遗工作方面的又一项重要成果,而且是恰逢其时顺势出现的重要成果。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认为有如下理由:
第一,从2011年中国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来,党政部门和社会各界对非遗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日渐深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指示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给予支持和扶持。非遗工作与我国社会文化建设关系的把握更加到位。文化主管部门在统领全国非遗工作方面的作为愈加积极主动,其结果就是我国的非遗工作在整体布局方面更有前瞻性规划和战略性眼光,动员社会各界力量的能力也更强。如今,对民众知识和实践的描述及总结已颇具规模,是时候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总结了。这部大辞典的出现,就是回应了这方面的需要。
第二,非遗的主要内容是老百姓的经验、知识、情感活动和相关操演,看上去似乎并不特别高深,事实上要想准确认识和科学描述非遗,却并不容易。无论国际学界对非遗的相关学理性思考和阐释,还是国内数量可观的非遗类研究成果,都说明对非遗的基本理论和特征、规律进行总结和把握,难度还是很大的。各地民众对非遗的认识,常囿于其文化生境和生态文化系统中,很难有较为全面的系统的认识,何况非遗的专业总结还需要以学界通行的术语和概念工具去把握。所以,在我看来,非遗既是“民众之学”,也是“专家之学”。说非遗是民众之学,是因为民众才是非遗的主人,具体体现为他们是非遗的持有人、实践者、传承人和改革者。专家也往往需要向民众请教,否则难以弄清楚非遗的来龙去脉、内涵功能、特点禁忌等。说非遗同时是“专家之学”,则是因为对非遗的全观把握、专业描绘、系统总结等,特别是在不同文化传统中进行比较的工作,非专业工作者很难做好。
第三,这部辞典的特点是:民众知识与专业知识的深度结合。从该辞典的撰稿人队伍构成上就可以看出,既有众多长期思考非遗专业知识和基本理论的专家,也不乏长期在非遗战线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士。这就保证了在这里所集中系统呈现的知识,既充满泥土芬芳,体现了民众的智慧;又具有在更大范围内可以共享、传播、比较、阐释的相对统一的格式和专业要求。
第四,非遗是汪洋大海,是民众长期创造和传承的知识和文化体系,没有人能够完整地掌握全部知识,但在实际保护工作和学术研究中,又需要经常查阅和了解相关知识,因而就格外需要有一个足够专业、足够全面、足够系统和足够权威的工具书,为众多希望掌握和了解相关文化内容的读者,提供比较准确的解答。所以说,这部辞典的出版是恰逢其时的。它以其学术把握的严谨性、科学性,既为非遗保护实践提供了实用的工具书,也为我国非遗保护的理论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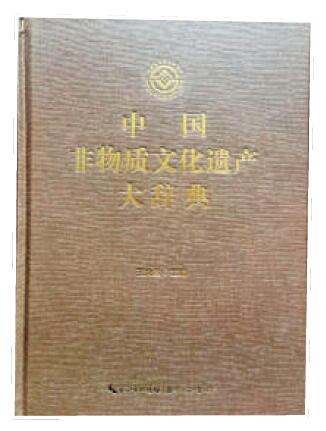










 吕梁红色经典新年音乐会暨《吕梁山大合
吕梁红色经典新年音乐会暨《吕梁山大合 2023年山西戏剧百事记
2023年山西戏剧百事记 “任跟心名家艺术工作室”揭牌仪式暨传
“任跟心名家艺术工作室”揭牌仪式暨传 大同市2024新年音乐会精彩上演
大同市2024新年音乐会精彩上演 孙业礼任文化和旅游部部长 胡和平不再担
孙业礼任文化和旅游部部长 胡和平不再担

 晋公网安备14010902001572
晋公网安备140109020015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