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士风与戏曲
2025-05-12 发表|来源:光明日报|作者:吴春彦作为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代表,“士”推动了文艺体式的生成、发展与繁荣,并将其笼罩于士风之下。明末清初是中国古典戏曲发展的黄金时代,“士”是戏曲活动的主导者与实践者。分析士群心态嬗变对戏曲创作的影响,透视士人习尚风貌主导下戏曲活动的走向,有助于追寻士风与文化流变的关联机制,探究传统文艺体式生存发展的规律。
一
明中叶以后,阳明心学的兴起开启了思想史的新篇章。其后,泰州学派的出现迎合了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时代对于思想解放的呼唤,其核心体现为肯定人欲、张扬个性。对于自我、个性、情欲的强化,成为晚明士子们沉湎声色、铺张奢靡之享乐风气的理论支撑。士林享乐之风,其背后是文化消费的繁荣。家班是士绅群体文化娱乐消费的重要方式,至晚明已成鼎盛之势,出现了诸如苏州申氏、无锡邹氏等享誉海内的家班。在文士享乐风潮的引领下,民间演剧之风愈盛。不管是活动组织、剧目选择,还是表演艺术的审美评判,士绅群体在民间演剧体系中都起着引领作用。民间演剧的盛行是士子享乐之风与戏曲嗜好对于市井的辐射与影响,是戏曲文化消费需求从士绅到市民的迁移。
王阳明高扬主体精神,倡导意志至上。他曾说:“我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罢。”(《传习录》卷下)这也成为晚明士大夫狂狷之风的思想根源。曲家邹兑金的杂剧《空堂话》中“空堂自觞”的张敉,其原型为苏州名士张献翼。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中记载其科举失意后,行为怪诞以抒不平之气。如若说这尚只是士子科举受挫后浮于表面的行为抗争,那意识层面的变化则更具说服力。晚明文坛巨擘汤显祖即发出“士有志于千秋,宁为狂狷,毋为乡愿”的呐喊(《玉茗堂文之五·〈合奇〉序》),主张破除迂腐之理的限制,凸显了主体意识的高涨。其对于自我情感、欲望和意志的关注,化为对于情的揄扬,《牡丹亭》将“情”视为突破“理”之束缚的有力武器,影响着历时几百年的明清传奇发展史。
世俗享乐并不能帮助晚明文士真正获得心灵的自由与解脱,万历而后,如陈垣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中所云,“禅风浸渗,士夫无不谈禅。”文士曲家们在承受了仕途受阻、官场倾轧、世事无常等众生之苦后,俗世的色欲之享难以抚慰,借戏曲创作而参禅说理、围绕“看破”与“解脱”建构主题成为晚明清初剧坛的普遍现象。吴梅在《中国戏曲概论》中即指出《南柯记》“畅演玄风”,为临川“度世之作”“见道之言”。又如《樱桃梦》等传奇,都增加度脱点化的情节,体现由迷茫困顿到醒悟解脱的禅悟过程。至于杂剧《有情痴》等更是淡化情节,成为阐发禅宗要义之作,充满了浓重的醒世意味。
二
四库馆臣在论及明代士风时指出:“隆、万以后,运趋末造,风气日偷。道学侈称卓老,务讲禅宗;山人竟述眉公,矫言幽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二)所论不免偏颇,却也道出了晚明士子沉湎于清谈、参禅的空疏风气。“理学”的教条与“心学”的空疏,以及由此诱发的士风衰退已被当时有识之士所认知,实学思潮应运而生。
东林学派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开实学思潮之端绪。高攀龙提出士大夫必须行实事,需“通世务,谙时事”(《东林书院志》卷五)。东林士人以强烈的济世情怀与牺牲精神,演绎出晚明政坛上打动人心的“东林气节”,直接影响了江南士风与世风,即便是幼童亦以此为仿效对象(王应奎《柳南续笔》卷三《东林气节》)。如此,求真务实、崇尚气节的士风与浮靡空疏之风截然分开,引领着士林风尚的转变。本为“娱情”的戏曲,也逐渐呈现出对于时事的关注。苏州派曲家是时事剧创作领域的佼佼者,他们以忠臣义士、市民运动、政治斗争入剧,所彰显的忠义节烈是东林气节在戏曲创作中的延续,对于世风的扭转大有裨益。时事风潮还体现在题材的拓展上,即便是明末言情剧如《鸳鸯绦》等,也不忘对于时事的渲染。在政治责任的传递上,复社袭自东林。然其士风走向则同时承袭了东林精神与浮靡风尚,将二者予以融合。复社诸子的文学或政治活动与秦淮乐妓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其对于戏曲审美风尚的品评与引领,推动了秦淮曲乐生态的形成。易代之际,复社诸子不乏壮烈之举,以实际行动表现了士林之不屈风骨,再现了东林精神。
清初,气节主导着士子的人生选择。士群的生命抉择不同,所展现的气度与风骨亦各异。对应文士群落士风的分化,戏曲也多有不同表现。对于清初遗民群体来说,戏曲选编与刊刻、家班蓄养、剧本创作等戏曲活动在排遣情思之外深有寄托,是遗民眷恋故国、反抗清廷的隐性表达,是晚明士风中现实关怀与气节风骨的显现。邹式金编选《杂剧三集》,多载遗老之作;冒襄于水绘园家班演出间,构建遗民的精神世界。对仕清士子而言,仕清的意图与情境不同,获得的风评与自我认知也大不相同,或可分为三类:一类为被迫出仕,然心怀愧疚者,如吴伟业,其戏曲作品成为兴亡之叹与矛盾心态的书写载体;一类为求平安富贵之贰臣;另一类则是晚明未有功名或官职而仕清的顺服者。后两类士群的戏曲活动大多不过是任情纵欲、轻狂享乐的晚明士风在清初的延续。
三
士林务实求实之风在清初时代语境下显现出更为深刻的内涵。顾炎武大力批判空疏学风是明亡之根本,倡经世致用之学,强化了对于文学功用、现实传统的回归。同时,清初三大儒无一例外高举“史”的旗帜,反复强调“尊史”对于“经世”的重要性。对于“史”的关注,迎合了清初士群形成的以反思为主题的时代心理与文化风潮。而戏曲在敷演故事、刻画人物上有着诸多便利,自然成为士群缅怀苦难、反思兴亡的重要载体。以“史”入剧、省思历史,进而达到救亡图存、济世救民的目标,成为清初诸多文士戏曲创作的共识。吴伟业为代表的抒情剧与苏州派为代表的历史剧,都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结合,以“史”的叩问与审视作为主题。而将历史反思与征实精神发展到极致的便是孔尚任的《桃花扇》,剧作以超脱而理性的胸襟反观历史,重现往日的诗韵风雅与道德气节,试图求得国之沦丧、风流云散的根本,甚而不乏对于人生、人性的哲学思索。
“整体论通常是以大量的省略、删减为条件的”(赵园《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在对士风的观照中,单一的整体概括并不严谨。在承袭晚明士风的同时,清初士风也呈现出不同的分化路径。梁启超在《新民说》所附《中国历代民德升降原因表》中指出明代“发扬尚名节,几比东汉”,而清代则“庸懦、卑怯、狡诈”。所论过于极端,亦陷入了整体论的困境,却也指出明清士风的流变动向。清初,晚明士风中的昂扬意气、崇高气节的淡化,士子强大文化自信与自我认同的消亡,已见端倪。浙江平湖名儒陆陇其云:“我国家初承明季之习,士风浮夸,不得不稍示裁抑,而士风日趋于下,砥砺廉隅者百不得其一,而刓方为圆者,比比而是……向以激昂为高者,今且以逢迎为高矣!”(《三鱼堂外集》卷二《养士》)黄宗羲有关士风走向的论述则更为直观而真实,“年运而往,突兀不平之气,已为饥火所销铄”“落落寰宇,守其异时之面目者,复有几人”(《黄梨洲文集·寿徐掖青六十序》)。清初李渔、万树等风流文人,对政治风云与社会变革置若罔闻,游走权贵之门,专注于风情喜剧的创作,借助误会、巧合等艺术手法表现才子佳人的离合情缘。其戏曲作品无非为显才或谋生的凭借,立意不高。值得关注的是,此类曲家多倡导戏曲对于风教的回归,李渔即强调戏曲需“有裨风教”(《笠翁一家言文集》卷一《〈香草亭传奇〉序》),“要使道学、风流合而为一”(《慎鸾交》传奇第二出《送远》)。这一理念似是对晚明放纵情欲观的反思与矫正,然其对晚明主情思潮的承袭却最终被引入了道学的牢笼,显现出此类曲家的局限性。至于尤侗为代表的文人抒情剧,不过是戏曲主体自我欲念的狭隘表达,曲辞营构技巧的高超掩盖不住格局的卑弱。如是,士风推动了传统文艺体式的生长与发展,递嬗之间也决定着其演进方向。
(作者:吴春彦,系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副教授)









 话剧《立秋》明星版太原首演拉开全国巡
话剧《立秋》明星版太原首演拉开全国巡 省城太原各剧场演出预告(2025年5月12日至
省城太原各剧场演出预告(2025年5月12日至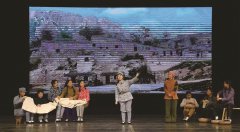 沉浸式情景剧《浩气长存报国亭》孝义首
沉浸式情景剧《浩气长存报国亭》孝义首 第3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终评在上海开幕
第3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终评在上海开幕 民族歌剧《小二黑结婚》复排,再现“清
民族歌剧《小二黑结婚》复排,再现“清

 晋公网安备14010902001572
晋公网安备14010902001572